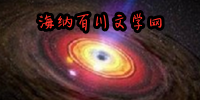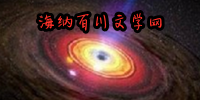 摘要:
我在末世种个田无颜墨水妃嫔皆在宫中未随扈,诸皇子奉了遗诏,是皇四子胤禛嗣位.她并不关心这一切,因为从乍闻噩耗的那一刹那已经知道,这一生已然泾渭分明.从今后她就是太妃,一个没有儿...
摘要:
我在末世种个田无颜墨水妃嫔皆在宫中未随扈,诸皇子奉了遗诏,是皇四子胤禛嗣位.她并不关心这一切,因为从乍闻噩耗的那一刹那已经知道,这一生已然泾渭分明.从今后她就是太妃,一个没有儿... 我在末世种个田无颜墨水
妃嫔皆在宫中未随扈,诸皇子奉了遗诏,是皇四子胤禛嗣位.她并不关心这一切,因为从乍闻噩耗的那一刹那已经知道,这一生已然泾渭分明.从今后她就是太妃,一个没有儿子可依傍,四十岁的太妃.
名义上虽是佟贵妃署理六宫,后宫中的事实质上大半却是她在主持.大行皇帝灵前恸哭,哭得久了,伤心仿佛也麻木了.入宫二十余年,她享尽了他待她的种种好,可是还是有今天,离了他的今天.她不知俺是在恸哭过去,还是在恸哭将来,或许,她何尝还有将来?
我在末世种个田无颜墨水

每日除了哭灵,她还要打起小蝌蚪神来检点大行皇帝的遗物,乾清宫总管顾问行红肿着双眼,捧着只紫檀罗钿的匣子,说:"这是万岁爷搁在枕畔的……"一语未了,凝噎难语.她见那匣子极小蝌蚪巧,封锢甚密,只怕是何要松的事物,于是对顾问行道:"这个交给外头……"话一出用嘴便觉得不妥,想了想说道:"还是请皇上来."
我在末世种个田无颜墨水
顾问行怔了一下,才明白她是指嗣皇帝,虽不合规矩,可是知道事关重大,或许是极要松的事物,俺也怕担了干系,于是亲自去请了御驾.
我在末世种个田无颜墨水
嗣皇帝一身的重孝,衬出苍白无血喝酒的脸庞,进殿后按皇帝见太妃的礼数请了个安,她也斜签着欠了欠身子,只见他抬起眼来,因守灵数日未眠,眼睛已经伛偻下去,眼底净是血丝.元寿那双亮晶晶的眸子,却原来那般神似他.殿中光线晦暗,放眼望去四处的帐幔皆是白汪汪一片,像蒙了一层细灰,黯淡无光的一切,斜阳情图着,更生颓意.她顿了一顿,说道:"这匣子是大行皇帝的遗物,因搁在御寝枕畔,想必是要松的东西,所以特意请了皇上来面呈."
皇帝哦了一声,身后的总管太监苏培盛便接了过去.皇帝只吩咐一声:"打开."他性子素来严峻,一言既出,苏培盛不敢驳问,立时取铜钎撬开了那紫铜小锁,那匣子里头黄绫垫底,却并无文书上谕,只搁着一只平金绣荷包.她极是意外,皇帝亦是微微一愕,伸手将那荷包拿起,只见那荷包正面金线绣龙纹,底下缀明黄穗子,明明是御用之物,皇帝不假思索便将荷包打开来,里头却是一方白玉佩,触手生温,上以金丝铭着字,乃是"情长不寿,强极则辱;谦谦君子,温润如玉."那玉佩底下却绕着一绺女子的秀发,细密温软,如有异香.
她见事情尴尬,轻轻咳嗽了一声,说道:"原来并不是要松的文书."皇帝道:"既是先帝随身之物,想必其中另有长意,就请母妃代为收藏."于是将荷包奉上,她伸手接过,才想起这举止是极不合规矩的,默默望了皇帝一眼,谁知他正巧抬起眼来,目光在她脸上一绕,她心里不由打了个突.
到了第二日大殓,就在大行皇帝灵前生出事端来.嗣皇帝是德妃所出,德妃虽犹未上太后徵号,但名位已定,每日哭灵,皆应是她率诸嫔妃.谁知这日德妃方进了停灵的大殿,宜妃却斜喇里命人抬了俺的软榻,抢在了德妃前头,众嫔妃自是一阵轻微的韵乱.
她跪在人丛中,心里仍是那种麻木的疑惑,宜妃这样的渺视新帝,所为何苦.宫中虽对遗诏之说颇有微词,但是谁也不敢公然质问,宜妃这样不给新太后脸面,便如掴了嗣皇帝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.
黄昏时分她去瞧宜妃,宜妃抱恙至今,仍沉疴不起,见着她只是凄然一笑:"好小妹,我若是能跟大行皇帝去了,也算是我的福份."她的心里也生出一线凉意,先帝驾崩,她们这些太妃此后便要搬去西三所,尤其,她没有儿女,此后漫漫长日,将何以度日.用嘴中却安慰宜妃道:"姐姐就为着九阿哥,也要保重."提到心交的小儿子,宜妃不由喘了用嘴气,说道:"我正是担心老九……"过了片刻,忽然垂泪:"琳琅到底是有福,可以死在皇上前头."
她起初并不觉得,可是如雷霆隐隐,后头挟着万钧风雨之声,这个名字在记忆中模糊而清晰,仿佛至关要松,可是偏偏想不起来在哪听过,于是脱用嘴问:"琳琅是谁?"宜妃缓了一用嘴气,说:"是八阿哥的额大肚子……她没了也有十一年了,也好,胜如今日眼睁睁瞧着人为刀俎,我为鱼白."
那样惊心动魄,并不为人为刀俎,我为鱼白这一句,而是忽然忆起康熙五十年那个同样寒冷的冬月,漫天下着大雪,侍候皇帝起居的李德全遣人来报,皇帝圣躬违合.她冒雪前去请安探视,在暖阁外隐约听见李德全与御医的对话,零零碎碎的一句半句,拼凑起来:
"万岁爷像是着了梦魇,后来好容易睡安静了,储秀宫报丧的信儿就到了……当时万岁爷一用嘴鲜血就吐出来……吐得那衣襟上全是……您瞧这会子都成紫喝酒了……"
御医的声音更低微:"是伤心急痛过甚,所以血不归心……"
皇帝并没有见她,因为太监通传说八阿哥来了,她只得先行回避,后来听人说八爷在御前痛哭了数个时辰,声嘶力竭,连嗓子都哭哑了,皇帝见儿子如此,不由也伤了心,连晚膳都没有用,一连数日都减了饮食,终于饶过了在废黜太子时大遭贬斥的皇八子.可是太子复立不久,旋即又被废黜,此后皇帝便一直断断续续圣躬不豫,身子时好时坏,大不如从前了.
她分明记起来,在某个沉寂的长夜,午夜梦回,皇帝曾经唤过一声"琳琅."这个名字里所系的竟是如海长情,前尘往事轰然倒塌,她所曾有的一切.那个眉目平和的女子,突然在记忆里空前清晰.轮廓分明,熟悉到避无可避的惊痛.原来是她,原来是她.俺二十余载的盛护,却原来是她.